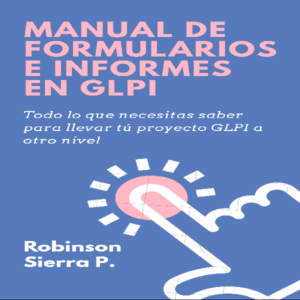一次特殊的采访,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残酷的现实撕去了我虚伪的坚强,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人,原来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这般地步? 在生死面前,我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先生,一封是写给自己。 给自己只写了几句话:“上帝给了你如此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你没有把它留下就走了,太遗憾了。你不能死,一定要挺过这场生死大劫!” 我的命运不济,所以一辈子都向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 2003年11月6日,我的人生更是跌到了谷底,几乎到了绝境。 这天,我家乡的老领导王文禄先生来找我,邀我写一篇著名心外科专家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的报告文学。说心里话,我不愿写这种遵命文学,而且我的身体很糟,经常发生心绞痛。可是王文禄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不好拒绝,只好跟着他来到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见面后,刘晓程院长第一句话却说:“雅文大姐,我一般不接受采访,你是家乡人,我不好拒绝。我问你,你准备用什么来写我?”一次特殊的采访,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残酷的现实撕去了我虚伪的坚强,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人,原来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这般地步?
在生死面前,我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先生,一封是写给自己。
给自己只写了几句话:“上帝给了你如此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你没有把它留下就走了,太遗憾了。你不能死,一定要挺过这场生死大劫!”
我的命运不济,所以一辈子都向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
2003年11月6日,我的人生更是跌到了谷底,几乎到了绝境。
这天,我家乡的老领导王文禄先生来找我,邀我写一篇著名心外科专家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的报告文学。说心里话,我不愿写这种遵命文学,而且我的身体很糟,经常发生心绞痛。可是王文禄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不好拒绝,只好跟着他来到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见面后,刘晓程院长第一句话却说:“雅文大姐,我一般不接受采访,你是家乡人,我不好拒绝。我问你,你准备用什么来写我?”
我想他绝非问我用什么书写工具,而是问我如何写他。我说:“我会用心去写你。”
听到这话,这位精明、干练、才华横溢的院长意味深长地笑了。
于是,两个素昧平生的家乡人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深、很透,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客套和粉饰。
采访结束前,我顺便将前不久我做心脏造影的CD片请刘晓程看看。他随后说出的一番话,却像一颗炸弹,一下子把我炸懵了。
“雅文大姐,你的心脏除了支架部位,还有六处病变,最严重的部位已经堵塞百分之九十,随时可能发生心梗。我建议你尽快做搭桥手术,而且要搭五至六个桥!”
我顿时觉得手脚冰凉,浑身直冒冷汗,心脏又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不久前,我刚刚在家乡一家医院做过心脏支架。
那天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医生和护士在我身边忙活,等待医生把心脏造影的“器械”从我大腿根动脉送进心脏,看我心脏有没有病变,我觉得就像罪犯等待法官宣判一样。几分钟后,医生出去了。只见满脸通红、神色极度紧张的先生周贺玉出现在手术室外的大玻璃窗前。
我急忙对护士说:“请您告诉医生,不用跟我爱人讲,他会受不了的。让医生跟我谈,我能挺得住!”
护士说:“看来你们感情真好,在手术台上你还为他着想呢。”
是的,没人知道我们经历过多少苦难,也没人知道我们有多么恩爱。后来先生告诉我,我被推进手术室,他的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哆嗦。看到医生出来,他手中的香烟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我知道我的心脏出了问题,但不知究竟有多大。
数分钟后,进来几位大夫,其中有我当运动员时的朋友脑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刘相轸医生。这位身材高大的汉子进门就拉住我的手,红了眼圈。
一年前,他的妻子文海美就是在一天早晨突发心梗去世的。当时他在电话里对我放声大哭:“雅文,天塌了!我救活过那么多人,唯独没有救活我的老伴啊!我真像天塌了一样啊!”
文海美是花样滑冰教练,当年曾拿过全国花样滑冰冠军。可她才六十岁却突然走了,这使我们非常难过。
而此刻,天塌的该轮到我了。
“雅文,你心脏的右前肢百分之九十五都堵了,侧肢有一根牙签细的血管支撑着,不然你早就完蛋了!”刘相轸快言快语地说,“我们不敢保证你去北京途中会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我给你做主,马上做支架!不要再犹豫了,千万别再发生海美的悲剧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唯有那根牙签一样细小的血管才是真实的,因为它连接着我的生命。奇怪的是,我曾做过多次检查,心电图从未有过异常,只是经常发生心绞痛,看来这心电图也会骗人哪!
医生给我心脏下了一个支架,但我仍然经常发生心绞痛,连洗澡都很困难,每次洗澡都像得大病似的,躺在沙发上半天都爬不起来。
听到刘晓程的这番话,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个拳头大的心脏除了一个支架,居然还有六处堵塞!这哪还是什么心脏,分明是一只破筛子啊!这么一台破碎的发动机,还能带动起我强大的生命吗?
我觉得生命随时可能离我而去,可我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还有多少创作计划没有实施,还有多少美好人生没有享受啊!
我觉得老天对我太残酷、太不公了。
我是来采访的,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重患。我无法接受这种落差极大的残酷现实。可我只能强忍着泪水,强装笑脸,对刘晓程说:“晓程院长,我才五十九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我不要多,再给我十五年就行。我太爱创作了。”
他说:“把你这颗破碎的心交给我吧。十五年太保守了,你准备再创作二十年吧!”我知道他在安慰我。
刘晓程找来内科副主任林文华医生当我的“保健医”,并给林主任下了“死令”,必须保证我在术前不发生意外,并一再叮嘱我:“争取尽快手术,以免发生不测!”
之后,我怀着满腔的惆怅与痛苦踏上了归途。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回去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满眼枯黄的秋色,我不由得回溯起自己的一生。
我一直苦苦地追求理想,追求高尚,把文学当成生命,不惜一切代价为之奋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从不绝望、从不气馁,我总是用孟子的话激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深信天道酬勤,深信“但得有心能自奋,何愁他日不雄飞”。
可是追求到最后,心已“破碎”却从未有过什么雄飞,一辈子都快走完了,也从没见老天降什么大任于我。本以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是老天降给我的大任,结果弄得身心憔悴,伤心欲绝,不得不打三起官司,而且得了严重的心脏病。现在,法院那边等待我去开庭,这边又面临着生死未卜的心脏大手术!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母,他们都没有心脏病,都是七八十岁才过世。我是运动员出身,一直坚持出操、跑步、游泳,身体一直很棒。我先生总是亲切地叫我“活兔子”。
三年前,我每天晚间都去游泳池游一千米。三年后的今天,却变成了一个亟待拯救、急需搭五六个桥的心脏病重患。
令我无法接受的并非是死亡,死亡是自然规律,上帝召谁去谁都无法抗拒,而是我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今天这种地步?我的心脏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坏的?
其中的原因才是我最痛苦、最无法接受的!
显示全部信息